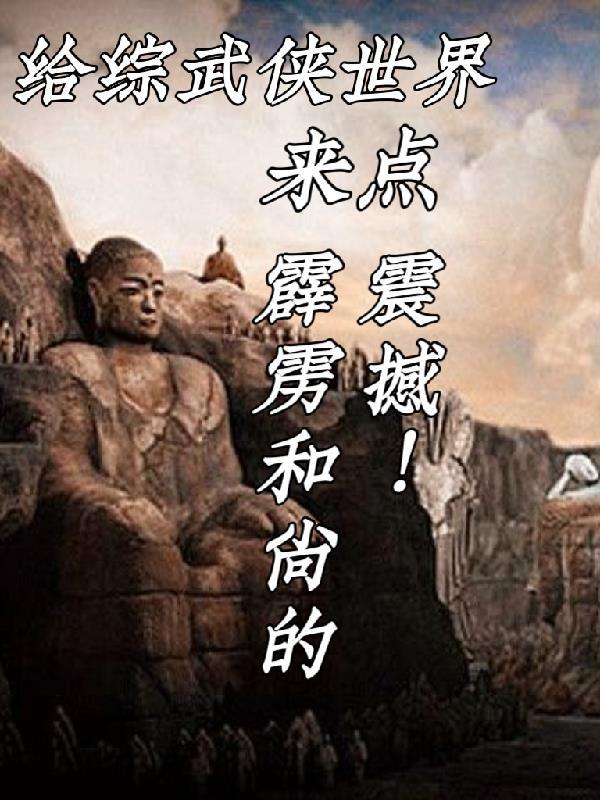笔趣阁阁>江都少年 > 第50页(第1页)
第50页(第1页)
宋山问:“怎么跑到这里来?”
路拾萤朝后堂的方向比划:“又疯了,我可不敢去。”
宋山叹气:“敬原就是这样。死性子,钻牛角尖,做事又追求完美……所以我才让他画工,不敢轻易让他走写意。你等着,过两天他初临山水时,又要作妖。”
果然,宋敬原在临帖上滞涩不通,转而画工。
他有好几副已经画好线稿的作品,就等着勾线。
手握小毫蘸了墨水准备下,该粗的地方卧不下去,细处又太生硬,甚至还有断的地方,于是越画越气,干脆全撕了。
撕完后,转去练山水入门,以“皴法”为主,结果点来画去,全似四不像。堂下不时传来“滋啦”一声,路拾萤和小王八一起屏气凝神,不敢吱声。
宋山说他心不静,不必强求,宋敬原一声不吭地上了楼。
喊他吃饭没人理,路拾萤推门一看,他倒在单词书里睡着了。
宋敬原是一个太要强的人。
立秋的这一天,蓬山路门口的一颗老竹黄了。
叶子纷纷剥落,融化在泥土中。
路拾萤对着种植书查阅许久,叹了口气:“之前下太多雨,淹过一次,这两天太阳又晒,长了黄斑。杆也不绿,歪歪倒倒的,算了,救不了了,砍了吧。”
宋敬原抬起眼:“不要砍。把它挪到后堂去。”
他放下书,从摇椅中起身,和路拾萤一起将这颗老竹移栽到后堂,紧挨小门的泥土中。
路拾萤这才注意到,小门边还有一颗矮矮的小树,看不出是什么品种,几乎全枯,只枝条上隐约抽出两片叶,不知有没有活的意思。
想来也是宋敬原不肯砍伐的一株生植。
宋敬原说:“万一呢,有枯树逢春那一天。”
他伸手,在枯枝之上系了一根红绳。
宋敬原开始琢磨山水,整天埋头书卷中研究山水画的皴法。
线皴、面皴、点皴……宣纸上密密麻麻画着各种石头和悬壁,宋敬原本人也和小花猫一样,满头满脸不小心蹭了许多墨水。
路拾萤一边奋疾书赶语文的周记作业,一边抬手不忘在宋敬原鼻头上刮一下:“你快去洗洗。”
宋敬原沉默片刻,忽地王八一样把头伸过来,在路拾萤刚买的衣服上猛蹭一把。
满身的墨,路拾萤“嗷”地惨叫一声。
路拾萤咽不下这口气,举着墨盒要呲宋敬原。两个熊孩子你追我打,根本没注意到门口有敲门的动静。
来访的客人见无人应答,只好自顾自把门一开。
这时,路拾萤恰巧抓住宋敬原的后衣领,一捏墨盒,“呲”的一声,一团墨水准确无误杀向堂下,在来者身上炸出一朵黑花。
路拾萤:“……”
宋敬原:“……”
客人黑着脸擦去手上的污渍,开口了:“我找宋山。”
一共三名来客,一个是熟人,两个不认识。
不认识的是一对父子,大人姓吴,约莫四十岁,偏胖,戴眼镜,文气;小孩叫吴孟繁,看着十四五岁,比宋敬原略矮半头,冷着一张脸不说话。
至于那个熟人——宋敬原摸了摸鼻头:“褚爷,您怎么来了?”
褚方元拄着拐杖吹胡子瞪眼:“你以为我想来!一进门差点被你这个小兔崽子糊一脸墨水!你师父会不会教徒弟!——你又是谁?”
拐杖冲着路拾萤去了,宋敬原只好替二人互相引荐。
点名道姓要找宋山的人不多,宋敬原只好把这一对父子请进堂下,煮了一壶茶,又找出春舟的点心,算是为某个路姓王八蛋的丢人行径赔礼道歉。
客套说了几句话,才知道,原来这位吴先生平日里素爱字画,也爱文玩,擅长写草书,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一位。
他的儿子吴孟繁受他影响,也从小练字学画。不日前,两人拜访褚方元的“绿扬斋”,偶然见到了宋山的字画——托褚方元代为出售的——大为惊喜,缠着人死缠烂打,终于问出了作者名姓,然后上门拜访。
路拾萤瞧见宋敬原不动声色地皱了眉:“他不在。”
“我们可以等。”
宋敬原面无表情地撒谎:“他出去找朋友了,估计会很晚才回来。或许不回来。”
吴孟繁忽然接话:“那我们就等到晚上。或者明天再来。”
这小东西年纪不大,说话老成,抬眼看人的时候一点表情没有,冷冰冰的,莫名透着一股傲气。
两句话都明里暗里带着锋芒,气氛一下子冷下来。
路拾萤开口打圆场:“不知道二位找老板有什么要紧事?其实可以让我们代为——”
没想到“转告”两个字来不及蹦出去,宋敬原打断他:“先讲清楚,我师父只做生意,别的念想一概不用打。”
路拾萤还没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,吴孟繁立刻回道:“那我也讲清楚,我这次来,就是要你师父收我做徒弟。”
一片死寂。
路拾萤终于看明白了——好家伙,这是逼人收徒来的。
宋敬原面色如常,但把手里的茶碗重重磕在案上时,“啪”的一声,胎底浅浅一道裂纹。这是忍了多大的脾气?连表面客气都不想装——路拾萤不由心想,这小兔崽子真会说话,一下把宋敬原的逆鳞翻了个底朝天。